業內動態
刑辯律師的惑與禍:執業困境漸露端倪
日期:2010-03-23 閱讀:2,729次
調查起因
北京律師李莊并非第一個因“撈人”獲罪的刑辯律師,為黎強辯護的法學泰斗趙長青,也并非第一個為涉黑嫌疑人辯護的名律師。然而,在重慶“打黑”進入司法環節之后,他們的遭遇似乎讓刑辯律師陷入了一場整體性的“危機”,這場“危機”既有加大執業風險的可能:李莊最終獲罪;又有聲譽受損的成分:趙長青一度在民眾樸素的善惡觀中被描繪成“黑社會的狗頭軍師”。
刑辯律師們被推到了風口浪尖,深水之下的行業暗礁和刑辯律師的執業困境也漸露端倪。
惑
“堅決不取證”?
3月20日晚從廣州趕回北京的律師楊學林,剛剛結束了一次令他極有成就感的開庭。他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十人的證人名單,其中六名證人成功出庭作證,并且被審判長當場認定有效。這是他從業以來的第一次。
楊學林估計,在同行當中,將“堅決不取證”當成座右銘執行的刑辯律師有70%到80%。幾年前,他也是其中一員;現在,他開始進行一些“小心翼翼地嘗試”。
會見、閱卷和調查取證,是2008年施行的新《律師法》中明確賦予律師的權利,但在采訪中,進行過刑事辯護的律師們,不約而同地對三者的難易程度進行了相同的排序:閱卷最易,會見次之,取證最難,尤其是“人證”。
證人在法庭上接受控辯雙方的反復詰問,這種港臺影視劇中的場景在內地法庭上并不多見。例如“李莊案”一審時,8名證人無一出庭作證,僅由控方宣讀了證人證言。
然而,對于無法接受“質證”的書面證言,卻很少有律師提出質疑。“證人不到庭,辯護律師完全可以質疑,上面的簽名是不是真的?甚至到底有沒有這個人?但是沒有律師會這么做。” 楊學林說,“這已經是一個慣例,如果你這樣做,那你比李莊還‘李莊’”。
辯護律師不僅難以要求控方證人,也很難找到愿意出庭的辯方證人。“作證費時費力卻沒有任何補助,我們的傳統也讓老百姓不愿牽涉到官司”,律師劉輝說,“而且,我們現在基本上沒有什么對證人的保護。” 在他接手的民事案件中,他的證人曾經被打過,他的當事人也曾經找人打過對方的證人,“面對公權力的時候,就更沒有人愿意作證了。”
此外,“人證”還極易給律師制造“雷區”。“如果證人跟我說的和跟檢方說的不一樣,法官通常會休庭”,他說,接下來,面對代表公權力的檢控方和律師,證人很可能會重新做出有利于檢方的供述,“那律師就危險了”。劉輝覺得,最好的辦法就是控辯雙方、法官、證人都到法院去當面談,并且錄音錄像,留下一份“護身符”。
上世紀80年代,律師作為“國家法律工作者”,和公檢法“平起平坐”。當時的《律師暫行條例》規定,律師的調查活動,“有關單位、個人有責任給予支持”;而1996年《律師法》出臺之后,律師變成了社會法律服務從業者,而律師的調查取證,必須得到相關單位和個人的同意。“人家不同意,你能怎么辦?雖然我們說公民有作證的義務,但這種義務是對公權力的,而不是對律師的。”劉輝說。
于是,律師們通常只能在檢方提供的現有證據材料之中尋找漏洞,組織辯護。
禍
“認真”你就輸了
盡管刑事辯護對抗性極強,但即便是在律師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,也“沒有哪個律師會盲目地去和公檢法鬧矛盾,除非你是個傻律師!”劉輝說。
無論是為了當事人的眼前利益,還是為了自己長遠的職業生涯,這種“較真兒”在律師們眼中,毫無用處。法律的確賦予了律師很多權利,但沒有哪一條規定當這些權利受到侵害時,應該怎么解決。“我們的法律很多,但是卻沒有一部‘當法律不被執行時怎么辦’的法律”,楊學林苦笑。
在行業中浸淫多年之后,律師們的身段越發柔軟。
在一次赴外地辦案時,當地的看守所所長拒絕楊學林會見當事人,理由是“辦案人員不在”。爭執無果,所長拂袖而去。楊學林沒有繼續較真兒,而是曲線救國。因為這個當事人身上不止一個案子,他就找到了負責另一案的檢察官,“借光”完成會見。否則,連當事人都見不到,根本無法向家屬交代。
劉輝說:“剛入行的時候,我是個很認真很負責的律師,現在,我是個很負責但不那么‘認真’的律師。”現在,律師們更樂于選擇庭外溝通,而非庭上的交鋒。“不傷和氣,庭前交流做得好,對當事人而言可能是最好的;比如提前和檢方探討適用的罪名,拿你自己的意見去說服他,有時候甚至能讓檢方放棄起訴。”劉輝說,而一味追求庭辯效果,“做得過火了,讓法官和檢方下不來臺”,則可能適得其反。
在日積月累間,律師們也摸索出許多法庭之外的策略,比如聯絡學界權威召開專家論證會對案件進行研討,形成《專家論證意見書》。至于效果如何,還得律師自己揣摩,“有的法官會覺得確實有道理,尊重專家的意見;也有的可能反而會不舒服:你還拿這個來壓我?”楊學林說。
更有“心計”的律師,甚至會打聽主審法官甚至法院院長當年求學時的院校和導師,專門去請這些老師來參與研討。
不過,無論刑辯律師的身段多么柔軟,依然無法避免和公權力代表的執業沖突中觸發的風險。
楊學林記憶中,最危險的一次辦案經歷是到北方某地,當時,他們已經是第三撥兒接手該案的律師。前兩撥律師都在辦案時遭到了不明身份者的毆打,其中第二撥兒律師遇襲后報警,當地110出警后,馬上“護送”律師們離開,一直等律師們的車上了高速才返回。而楊學林和他的同事們最終也狼狽逃離,在他之后接手該案的律師,還沒到達當地,就在大巴上被人圍毆,受傷入院。
“我只能把我能做的做到極致,做刑辯律師要在乎結果,但是不能太追求結果。”楊學林說。
辯
記者:在重慶“打黑”中,專門提到了北京律師爭相赴渝接案的問題,為什么外地的當事人熱衷于請北京律師到當地去辦案?
劉輝(北京市燕園律師事務所合伙人):我不敢說絕對,但是大多數北京律師的業務水平確實要比當地律師高,人脈關系也更廣。
楊學林(北京市首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):不可否認有看中北京律師“關系”多的因素,有些當事人就是希望通過北京的律師,把案子往上面透一透。
另外,我現在主要接一些弱勢群體因為環境、土地等問題在維權過程中引發的刑事案件。有些案子在當地有了政治因素,當地甚至會給律師開會打招呼,讓律師不要去接,那么當事人在本地根本找不到律師。
記者:刑辯律師在法庭上解脫貪官、“黑老大”這樣的“壞人”,即便知道這是公民的權利,但普通人從感情上仍然很難接受,那么這種辯護,對于維護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有什么樣的意義?
劉輝:他是個“壞人”你還為他辯護?大多數非法律界人都不能接受。事實上,律師、法官和檢察官是一個共同體,只不過他們的分工不同,作為公訴人,你就是要千方百計去追求當事人有罪;辯護律師也是通過各種法律手段去維護當事人的利益;法官則根據法律進行裁判。三方是通過辦個案,共同利用法律去維護公平和正義。
延伸調查
“撈人”的黑白之辯
伴隨李莊案發,“撈人”這個詞頻頻見諸報端,并蒙上了一層灰影。這個在普通民眾眼中頗有點神秘色彩的語匯,對于大多數刑辯律師而言,只不過是司法程序“取保候審”的通俗說法。
北京各大看守所附近,都有不少打著律師招牌的小門臉兒,就近在嫌疑人家屬中間招攬“生意”,而嫌疑人家屬最迫切的訴求就是請律師幫忙“撈人”。 “一旦嫌疑人被‘撈’出來,即取保成功,最后又判了緩刑,就等于不用進去了。”律師劉輝說,因為被告人最終被判處的刑期由被羈押之日算起,“取保候審”的時間也同樣算在刑期之內,“取保”成功就意味著減少當事人在看守所內失去自由的時間。
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中,對“取保候審”條件有明確的規定。通常律師在接手刑事案件時,只要符合條件,都會為當事人提出“取保”申請,但這個正常的司法程序卻在現實中有些“變味兒”。
有11年從業經歷的劉輝,總結出了三條在正常情況下最容易“取保”成功的條件:第一,未成年人,尤其是在校學生;第二,本地戶籍且最終刑期很可能在三年以下;第三,情況極特殊者,比如殘疾人、有重病的老年人等可能給看守所帶來“麻煩”的嫌疑人。
除此之外,其他情況的“取保候審”都不太容易獲批。在他看來,可以理解的原因是“取保”會給案件偵辦帶來風險,“工作在第一線的公安干警真的非常辛苦,壓力也大,他們好不容易抓了人,現在放了,萬一跑了,去哪兒找?”而另一方面,也的確存在有人希望借此謀求灰色收入。
在百度百科對于“取保候審的條件是什么”的回答中,獲選最佳的答案除了列舉法律條款之外,還做了如下說明:如果案件剛開始偵查,嫌疑人已經被拘留,但是沒有自首、立功、賠償等情節的,申請取保候審,基本沒有希望;如果已經逮捕,那么除了中國特色的“溝通”,就更不要奢望取保候審了。
一邊是迫切希望“把人弄出來、少遭罪”的嫌疑人家屬;另一邊是操作空間有較大彈性的“取保候審”,這樣一來,律師或打著律師幌子吹噓自己有關系的“訴訟掮客”們收錢“撈人”就有了市場。
“其實,自稱有關系能‘撈人’的‘能人’大多數并不是律師。”劉輝說,“而恰是這些人破壞了律師的整體形象。”
每年,全國各地幾乎都有因“撈人”引發的詐騙案。上周,北京大興法院就開庭審理了一件,而涉案者鮮有真正的執業律師。
業內熱點
法治熱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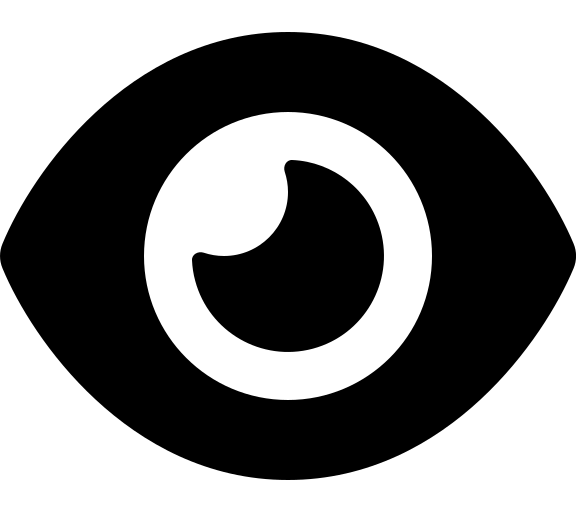
 中國律師身份核驗登錄
中國律師身份核驗登錄





















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
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