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娛動(dòng)態(tài)
常修從醫(yī)之德 常懷律己之心
日期:2020-05-07 作者:張剛 北京盈科(上海)律師事務(wù)所
“職業(yè)化與專業(yè)化——上海律師和上海醫(yī)生的對話”主題活動(dòng)
我記得讀法律碩士的時(shí)候,法學(xué)老師在課堂上講到,人類社會(huì)離不開的三種職業(yè),人的一生難免會(huì)和他們打交道:醫(yī)生、律師和牧師。醫(yī)生救死扶傷,治療的是人的身體出現(xiàn)的疾病,人食五谷雜糧,難免會(huì)生病;律師以法律為職業(yè),解決的是人的行為帶來的社會(huì)矛盾,這個(gè)復(fù)雜的世界,人們越來越認(rèn)識(shí)到法律才是維護(hù)人們合法權(quán)益的最有力的武器;牧師解決的是精神問題和信仰問題。
老師還說,從這個(gè)意義來看,律師這個(gè)職業(yè)還是很有前景的,永遠(yuǎn)都不會(huì)失業(yè),所以我畢業(yè)后當(dāng)了律師。
我覺得很多職業(yè)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,今天我就談一談,醫(yī)生和律師這兩個(gè)職業(yè)的關(guān)系。
我們都知道,醫(yī)生是一個(gè)偉大的光榮的職業(yè),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,他們作為逆行者,不畏生死,堅(jiān)守使命,始終沖在抗擊疫情的第一線,是戰(zhàn)勝病魔的中堅(jiān)力量,這是我們有目共睹的。
作為律師,我不想蹭熱點(diǎn),不想鑿壁偷光,也不想與他們相提并論,我只是想探討兩種職業(yè)的關(guān)系,進(jìn)而督促自己努力向他們學(xué)習(xí)從醫(yī)之德,堅(jiān)守職業(yè)道德操守,熱愛本職工作,嚴(yán)于律己,全力以赴,為法治建設(shè)貢獻(xiàn)微薄之力。
醫(yī)生和律師看似毫無關(guān)聯(lián),但兩者職業(yè)屬性相似。
首先,不是任何人想干醫(yī)生和律師就能干的,醫(yī)生和律師的行業(yè)準(zhǔn)入門檻都很高。要想從事醫(yī)生職業(yè),首先要有醫(yī)學(xué)教育經(jīng)歷,通過醫(yī)師資格考試和實(shí)習(xí)后才能執(zhí)業(yè)。律師也是,要有法學(xué)本科以上教育背景,通過全國第一大考:法律資格考試,然后必須實(shí)習(xí)一年以上,才能申請執(zhí)業(yè)律師。
我不了解醫(yī)師資格考試的內(nèi)容,估計(jì)也不容易,但我知道法考的難度。有人統(tǒng)計(jì)過,法考的考試內(nèi)容涉及到的法律法規(guī)以及司法解釋有300多個(gè),復(fù)習(xí)資料堆起來足有兩米多高,復(fù)習(xí)一遍,快的兩個(gè)月,慢的三個(gè)月,看完后面的,前面的已經(jīng)忘得差不多了,每年有四五十萬人參加,通過率10%左右。可見法考的難度之大。
但是,我仍然認(rèn)為醫(yī)生的專業(yè)門檻更高,醫(yī)學(xué)知識(shí)更為深?yuàn)W,難以企及,一個(gè)普遍的現(xiàn)象就可以證明這個(gè)觀點(diǎn):我見過醫(yī)生通過司法考試,轉(zhuǎn)行做律師的很多,我們律所就有好幾個(gè)律師,原來是醫(yī)生,現(xiàn)在專做醫(yī)療事故的案件,但我還沒見過律師轉(zhuǎn)行去做醫(yī)生的,肯定有,估計(jì)不多。
持證上崗是這兩個(gè)職業(yè)的共同要求。當(dāng)然不是說,有證的都比無證的厲害。難道說,扁鵲,張仲景,孫思邈,李時(shí)珍在古代沒有證,就抹殺他們在醫(yī)學(xué)界的地位?不是,有些是對人們的命運(yùn)會(huì)產(chǎn)生重大影響的職業(yè),比如醫(yī)生、律師、教師、記者、會(huì)計(jì)等,需要規(guī)范,需要注冊,需要政府的監(jiān)督和管理,所以設(shè)置了門檻。有人說,一些民間郎中沒有拿到證,但是有自己的一套神奇的治療方式,可能是祖?zhèn)髅胤剑赡苁亲约旱陌l(fā)明,只要有療效就應(yīng)該鼓勵(lì)執(zhí)業(yè),不必在乎什么醫(yī)師證,甚至提出廢除相關(guān)法律。
作為律師,我認(rèn)為,現(xiàn)在是法治社會(huì),任何人必須在現(xiàn)有的法律框架內(nèi)活動(dòng),禁止一切形式的非法行醫(yī),如同律師沒有執(zhí)業(yè)證就不能以律師身份接受當(dāng)事人的委托,收取律師費(fèi),代理案件一樣。我們絕不能回到過去,無視規(guī)則,無視法律。依法治國的理念任何時(shí)候都不能被拋棄,遵紀(jì)守法是每一個(gè)公民應(yīng)盡的義務(wù),不能因?yàn)橥话l(fā)事件,就可以把法律拋到九霄云外,任何人都可以任意作為(這是疫情期間作為法律人的一點(diǎn)感慨)。
有人會(huì)說法律不完善,法律規(guī)定的有問題,應(yīng)該修改法律或規(guī)則云云,我們說,那是立法者的事情,你們可以事后提出建議,但是現(xiàn)在不能隨意挑戰(zhàn)法律和規(guī)則。同理,既然參加了國際組織,就要遵守游戲規(guī)則,否則只能是自食其果,接受懲罰,付出代價(jià),這是血的教訓(xùn)。絕不能感情用事(這是對最近熱點(diǎn)事件的一點(diǎn)感慨)。
但是,我并不是說,江湖郎中的醫(yī)術(shù)并不高明,也不能說不能推廣使用,只要確實(shí)能治病救人,完全可以在法律框架內(nèi)采取變通的方式解決問題,不能一味排斥,更不能一棍子打死。
醫(yī)生和律師在理念方面也是相通的,有異曲同工之處,可以互相借鑒。
戰(zhàn)國時(shí)期的韓非子在《扁鵲見蔡桓公》里寫到,一日扁鵲見到蔡桓公,告訴他有一個(gè)小毛病在他皮膚上,蔡桓公不信,過幾天,扁鵲再見他時(shí)告訴他,毛病到了肌肉里,蔡桓公還是不信,再過幾天,扁鵲告訴他,他的病到了腸胃,他還是不信。后來蔡桓公再見扁鵲時(shí),扁鵲跑開了,有人問扁鵲原因,他說蔡桓公的病到了骨髓,已經(jīng)沒法治了,我趕緊跑。果然不久蔡桓公就病死了。
很多人讀了這個(gè)故事,很容易得出結(jié)論:君王不信任扁鵲乃至于此。
我從律師職業(yè)的角度解讀一下這個(gè)故事。
從這個(gè)故事里我們可以看出三種法律服務(wù)模式:法律風(fēng)險(xiǎn)管理,法律顧問和爭議解決(或叫打官司)。
什么是法律風(fēng)險(xiǎn)管理,簡單來講,就是對企業(yè)的潛在法律風(fēng)險(xiǎn)進(jìn)行識(shí)別、評(píng)估后,提出解決辦法,預(yù)防法律風(fēng)險(xiǎn)的一種法律服務(wù)方式。律師這個(gè)時(shí)候介入服務(wù),叫事前防范。從醫(yī)學(xué)來說,叫體檢,很多人每年都要進(jìn)行體檢,看似健康的身體,一查才知道都是亞健康,幾乎都存在潛在的健康風(fēng)險(xiǎn),相當(dāng)于扁鵲說的小毛病,這個(gè)時(shí)候比較容易調(diào)理。
法律顧問,比較好理解,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很成熟,越來越多的企業(yè)聘請律師做他們的法律顧問。律師的工作主要是審查修改合同,接受法律咨詢,收發(fā)律師函,對發(fā)生的糾紛提出解決方案等等。這個(gè)時(shí)候,企業(yè)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了問題,有這個(gè)法律需求,問題還沒有全面爆發(fā)出來,需要律師保駕護(hù)航。這叫事中防范。
打官司,就是矛盾爆發(fā)了,發(fā)生了不可調(diào)和的糾紛,到了法院或仲裁委,需要律師介入,這屬于事后法律服務(wù)。相當(dāng)于病已到腸胃,人需要住院,需要緊急治療的階段。
幾千年過去了,我們從未吸取教訓(xùn),用黑格爾的話反過來說,人類唯一能從歷史中吸取的教訓(xùn)就是,人類從來都不會(huì)從歷史中吸取教訓(xùn)。我們只是在火燒眉毛的時(shí)候,才會(huì)想到律師。如同人等到病入膏肓的時(shí)候,才去醫(yī)院找醫(yī)生看病一樣。
律師同醫(yī)生一樣,也需要極高的職業(yè)道德操守。
我不想窮盡所有內(nèi)容,只需談幾個(gè)要點(diǎn)。醫(yī)生,對癥下藥,童叟無欺,律師受人之托,忠人之事,誠信勤勉提供法律服務(wù)。醫(yī)生和律師都要遵守法律,尊重同行。醫(yī)生對患者,律師對客戶,都需要保護(hù)隱私,保守秘密。醫(yī)生對待自己的病人,不論身份,救死扶傷是醫(yī)生的天職,哪怕他是一個(gè)窮兇極惡的敵人,或是一個(gè)即將奔赴刑場的死刑犯,都有被救治的權(quán)利。
律師也是,全心全意去維護(hù)自己當(dāng)事人的合法權(quán)益,是律師的天職,哪怕他是一個(gè)十惡不赦的殺人犯,民憤極大的貪官。這一點(diǎn)律師很容易被誤解,其實(shí)律師不是去“為壞人說好話”,而是正確實(shí)施法律,讓被告受到應(yīng)有的對待,沒有犯罪,就不應(yīng)該被定罪處罰,罪輕就不應(yīng)該被重判,避免或減少冤案的發(fā)生。
醫(yī)生和律師主要有兩點(diǎn)不同。
醫(yī)生的公益性特點(diǎn)較為明顯。我們對他們從不吝嗇贊美之詞,我們這個(gè)社會(huì)確實(shí)需要白衣天使這個(gè)崇高的職業(yè)。醫(yī)生的公益性體現(xiàn)在,醫(yī)院是公益事業(yè)單位,不是營利性單位,以政府投入為主,醫(yī)生是事業(yè)編制,拿的是工資,而肩負(fù)的是全民的公共衛(wèi)生和健康事業(yè)。
而人們對于律師可能有太多的不了解,甚至誤解。律師事務(wù)所是合伙企業(yè),律師是合伙人,通過法律服務(wù),獲取當(dāng)事人的報(bào)酬。但是,律師也肩負(fù)著一些社會(huì)責(zé)任。從大的方面來說,就是肩負(fù)著維護(hù)社會(huì)公平和正義的責(zé)任,小一點(diǎn)就是經(jīng)常參加一些法律援助案件,參加一些社會(huì)公益性活動(dòng),提供一些免費(fèi)的法律咨詢和幫助,甚至直接參與扶貧活動(dòng)。比如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,全國的律師積極捐款捐物,有的協(xié)助社區(qū)或機(jī)構(gòu)進(jìn)行執(zhí)勤管控。我沒有統(tǒng)計(jì)其他律所的捐款數(shù)額,我知道我們律所的律師僅是捐款就超過300萬,其他捐贈(zèng)的物資不算。
相對于醫(yī)生,律師還有一個(gè)特點(diǎn),就是大家都認(rèn)為的,律師是一種自由職業(yè)者。醫(yī)生目前還沒有放開,還在探討中,將來也許會(huì)有。在人們看來,自由好像是律師最大的福利。其實(shí)這個(gè)自由是相對的,律師沒有上下班,因?yàn)橐恢痹诩影啵蓭煕]有假期,因?yàn)橐恢痹诼飞希蓭熓抢习澹彩菃T工,自己交社保,自己發(fā)工資。律師有閑暇的時(shí)候,那是因?yàn)闆]有案子,沒有案子就沒有收入,沒有收入怎么養(yǎng)家糊口?一個(gè)普通律師的任務(wù)就是天天拼命找案子,找到案子,拼命做案子,律師從來沒有輕松自由過。
比如這次疫情期間,雖然宅在家里,但一刻也不敢松懈,學(xué)習(xí)最新法律法規(guī),研究最新案例,寫專業(yè)文章,不斷武裝自己的頭腦,隨時(shí)準(zhǔn)備為客戶服務(wù)。律師這個(gè)行業(yè)就是這樣,不要以為自己是資深律師,就放松了學(xué)習(xí),如逆水行舟,不進(jìn)則退。
好了,有當(dāng)事人加我微信咨詢我法律問題,她不分晝夜給我留言,午休時(shí)給我打電話,急切地要請我代理這個(gè)案子。我仔細(xì)地研究了案情和材料,精心制作了方案。發(fā)過去后,幾天不見回音,我問:“有什么意見嗎?”
過了半天,那邊回:“張律師,能見面談嗎?”
我說:“這個(gè)非常時(shí)期,不方便見面的。”
“很多事情,我想還是當(dāng)面交流最好,微信和電話也說不清。再說我不認(rèn)識(shí)你,不見面,我怎么相信你啊?“
我說:”再等幾天,這個(gè)疫情也快結(jié)束了,等全面復(fù)工了,我們見面談,好吧?“
終于有一天,我的臨時(shí)出入證換成了出入證,出門不受時(shí)間限制了,我趕緊約那個(gè)客戶,不料,那邊回復(fù):我不需要律師了!
我見到網(wǎng)上有人曬出一個(gè)圖表,說是這個(gè)疫情影響最嚴(yán)重的行業(yè),第一是養(yǎng)殖業(yè),第二是電影業(yè),第七是律師。不管這個(gè)排名是否科學(xué),起碼他懂得律師的尷尬處境。
但我每天還是像往常一樣地起床,工作,學(xué)習(xí),看書,吃飯,睡覺,思考,寫作,因?yàn)槲倚闹幸恢睉汛е诖拖M谕麘?yīng)該是我們前行的最大動(dòng)力。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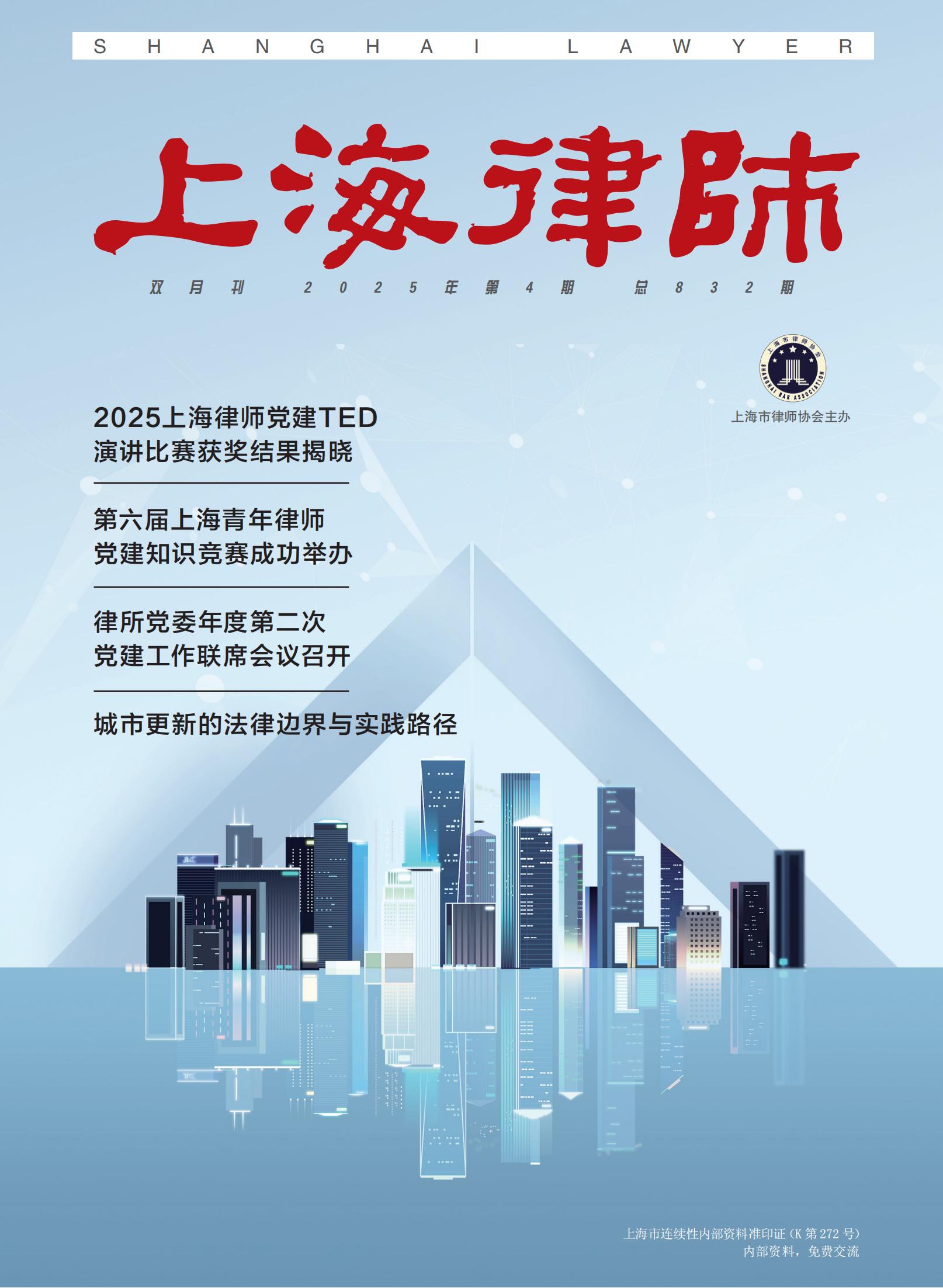
 滬公網(wǎng)安備 31010402007129號(hào)
滬公網(wǎng)安備 31010402007129號(hào)
